[经管]读书笔记||宿命与孤独——读《百年孤独》有感
《大哲学家·康德》一章中有言:“人类理性的命运,要么冥思苦想,做鬼脸,要么胆大妄为,追逐过于宏伟的事物,间歇空中楼阁。”

所谓理性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充满着荒谬,那么是否可以认为《百年孤独》中的荒谬也透露出一些宿命式的理性呢?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早已在羊皮纸上写有,谁会富裕,谁会疯狂,谁会爱上谁都已注定。家族七代人里,无非两种命运:死于非命,孤独终老。宿命论的东西总带有一种绝望的诱惑,那种反抗命运的刺激感总能挑拨起人隐藏的冲动。我们不接受脱离世俗的奇怪,却允许最奇怪的事情成为经典,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靠它的奇怪活过来的。
我有些“变态”地喜欢故事中孤独终老的结局。顾彬有言:“世上美丽和伟大的东西必然是孤单的,但这种孤单本身并不是问题,而问题的所在是无人知晓这种美丽和伟大,相反人人都可以抱怨世界的虚无。”试想,当世界总是将其难堪的一面,鲜血淋漓地摆在你的面前,炫耀式地居高临下,像是要看看一个敢于反抗的人,不得不直面命运的摆布,还不能非议自己的人生,是一种怎样的绝望。这种绝望能摧毁一个人,也可以塑造一个人。我喜欢那种自生命深处迸发的活力,纵使结局是悲剧。
马尔克斯曾说:“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,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。”我热爱这种拼尽一切却不论回报的激情。这世界上总存在一种仁慈,焦虑地爱着这个世界的好人,在确认一事为善之前,什么都不做,也不可能强求他人去做。他只会疲劳地行善,把善奉送在他人面前,期待他人有朝一日良心发现。纵然外在世界犯着滔天大错,他也不会认为这个世界应当被怒目以对。
“有的人总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成为圣人,对于这种行为本身,奥利维拉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。但他还以这种行为,并把它排除在本人行为之外。”我们都无法得知,一个良善的人在“不应该”和“不值得”间,是否做过两难的选择。但我却坚信,但凡拥有这种近乎疯狂的善良的执念的人,都不会是价值二元主义者,觉得这世界怎么胡来都行。
我常常觉得一个孤独的人,往往肩负着别人不愿去承担的东西。这东西可以选择不背,但确实也需要有人来背。我总觉得那些孤独地坚持着为这世界奋斗的人,总是自觉地将世界犯的错,默默地抗在自己的肩上。他们认为自己处在世界当中,扮演着它的一部分,无论如何总有自己不自觉生长出来的不对,来助长这个世界的不对。
他们的愤怒是对自己的愤怒开始的,他们的谴责是对自己的谴责开始的,他们的宽容是对自己的宽容开始的,他们的辽阔是从把自己清空,让世界开始辽阔开始的。邱妙津在《蒙马特遗书》中写到:“每个人都只能也必然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,而且,那负责是独自在自己内心进行而无关乎他人的……唯有你自己才能‘审判’你自己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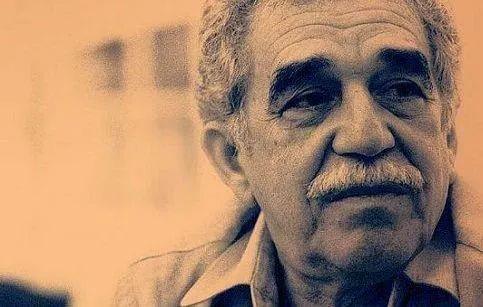
我相信命运的不可抗力性,但我也热爱着绝望的反抗;我害怕只有一个人的世界,但我也绝不放弃孤独所带来的自我审判。人生虽说会遇到很多人,会有白首不分离的美好,但是本质还是孤独且仅属于自己的。人可以有很多追求,但是找寻到自我却是与生命共存的。
文字:范婷睿
编辑:罗倩

